记者 丘濂 摄影 王大勇
期刊 三联生活周刊 2016(31)102-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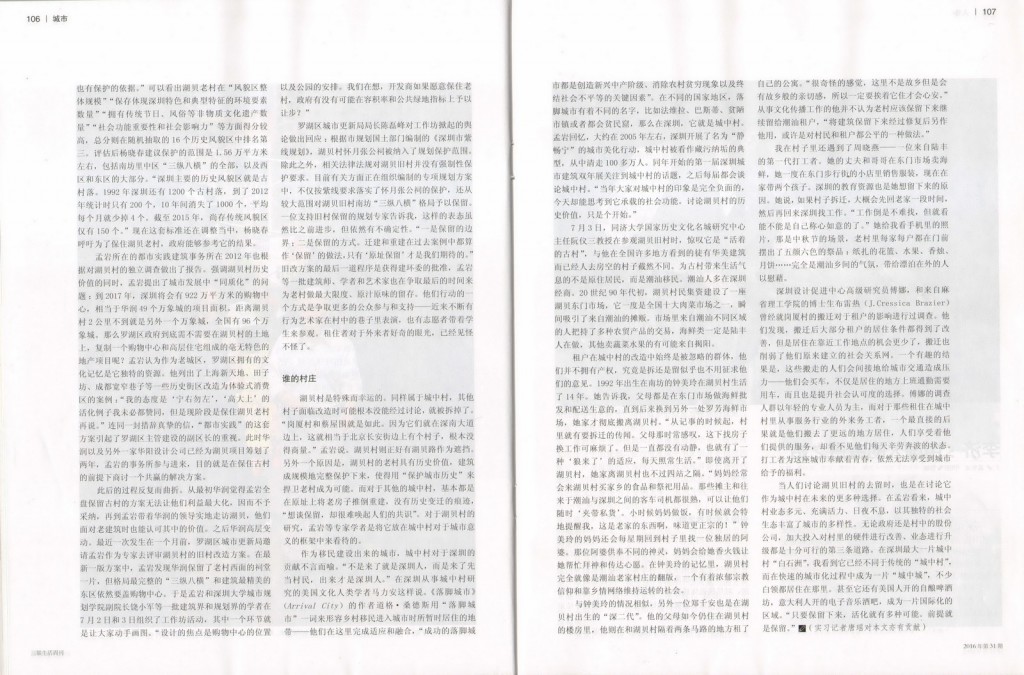
当人们讨论湖贝村的改造前景时,也是在讨论深圳300多座城中村的未来。拆迁以及开发,将不再是唯一一条道路。
城中古村
如果没有人带领,你很难找到湖贝村的旧村。尽管这片开阔的村子就在深圳著名的东门商业街旁边,处于罗湖区的中心地带。
村子的正门在湖贝路上分叉出去的一条小巷里,一不留神就会错过。早晚时间,村口拜神的香火会格外旺盛。当看到一团升腾的烟雾,便知道摸到湖贝老村的入口了。进出村子的围门门洞被改成了朝拜的殿堂,沿着墙壁的架子上一侧放着财神、关公、观世音,另一侧有天地和土地公。“这些都是潮汕人带来的神明,过去村民是不在这里拜的。不过我们进出村子,都会双手合十的,很灵的。”湖贝村的书记、村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张齐心说。
穿过门洞,便犹如时光倒流般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以门洞正对的甬道为中心轴线,老村最核心的区域是一片有着“三纵八横”布局的广府系坊巷排屋。湖贝村的历史开始于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第十三祖张怀月和弟弟张念月在湖贝开基立村,这一脉张氏族人则最早可以追溯到始祖张挥、太祖张良、张衡、张九龄、张九皋等人,他们从北方辗转迁徙而来。能选择湖贝这片土地自然是因为风水好的缘故。《湖贝村村史》的编纂者之一、村民张炜良画了一张村子的草图给我,可以看到历史上村子南边有一片叫作田浸湖的水面,村子从最早的“三纵八横”继续向西和向东扩张,相继形成了西坊和东坊,犹如一块打开的贝壳。“湖贝村”的名字虽不可考,但依湖而建的村庄形态能够体会出名字的贴切。
20世纪80年代,为了满足村民建设住房的需求,湖贝村在旧村东面和北面相继获得了宅基地,东面建成了湖贝新村,北部则称北坊。无论西坊、东坊、北坊还是湖贝新村,一开始建成的都是二三层的贴面瓷砖小楼,普遍又经过90年代中期一到两次的重建,成了七八层高的楼房。南坊则奇迹般地保留了老屋。“三纵八横”的区域最完整——尽管有了后来租户们的私搭乱建与小规模的维修,仍可看出建筑的精美:门楣上都有雕花,是鸟兽、花草、人物等各种祥瑞图案。张炜良说,老屋原始的设计和材料考虑到了湿热地区的通风需要,“瓦顶透气,墙体有青砖、泥砖和三合土舂墙几种,夏天也比较凉爽”。中区的“三纵八横”外,南坊的西区祠堂周边以及东区,都有精良建筑留下来。尤其是东区的建筑规格更高,如果是三到四层的花岗岩做基底,便可知晓这是原来村里的大户人家。
南坊的建筑能保留至今,不能不说是运气的结果。罗湖区是深圳成为特区后最早建设的地区,当时的深圳所谓“一区一县”,就是罗湖区和宝安县。湖贝村原来地盘广袤,因为处于罗湖区的黄金位置,成为首先失去土地的一批村庄。张齐心告诉我,南坊实际从1992年起就属于政府划定的旧村改造范围。“政府有改造的冲动,但实施起来却有困难,土地权属复杂是个重要原因。”没能改造,好处是如今在高楼林立的罗湖,留下了一片历史有550年的古村;而弊端就是村民们一直都有怨言。“南坊处于改造的蓝线之内,不允许村民重建楼房。村民收来的租金低,却要承担巨大的风险责任。”一位名叫张锦松的村民和我说,他在收房租之外,都不愿意踏进老村。“40多平方米的房子,我租给一个人,他又转租给另外6人,我实际只能收到700多块钱的租金。”老村里街道狭窄,电线密布,排水系统差,一下雨便污水横流。“偷电是常事,南方电网找到村里想要治理,可根本抓不过来。”2004年,南坊的平房里发生了一起偷电引起的严重火灾,导致一名女童丧生。“作为房东,我们都是提心吊胆,一旦着火了怎么办?刮台风房子塌了怎么办?”
走在老村,那些建筑能勾起张齐心许多回忆。“你看门头上雕的雀鸟,小时候我顽皮还拿棍子给捅下来一只呢!”张齐心在1983年搬到了新村盖的小楼,2003年后住进了商品房彻底离开村子。如今无论在新村还是老村都很难见到本村村民了。湖贝村的村民散居在深圳,还有很大一部分在港澳台和海外。在村子里随机问到的人都是租客,唯一一个村民聚集的地方是老年人活动站——每天下午本村老人都会从四面八方赶来,在这里打麻将。除了收租,祭祖活动是村民们回到老村的唯一理由。“家中添丁,村民都会来祠堂禀告祖先。”张齐心说。而最盛大的祭祖是在重阳节,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的张氏族人都会回到湖贝,在祠堂里给祖先上香后,会在湖贝新村的空场上围坐在一起吃盆菜,每年都有700多桌。
深圳是带状的一条,北面有山,南面有海,2005年还为自己划定了一条生态线,相当于束缚住自己向外扩张的手脚。经过多年的发展建设,罗湖区的用地已经十分紧张,于是政府将眼光重新投向湖贝。2011年央企华润置地进入,湖贝改造事宜正式提上日程。在2012年的表决大会上,超过97%的湖贝股份公司股民举手同意改造并签字。旧村和新村都在改造范围之内,楼房按照1∶1的面积来赔偿,瓦房的标准是1∶2.33。“村民普遍满意,又有一批千万富翁诞生。剩下不同意的村民基本是利益问题,比如自家有门面房,嫌赔偿的价格不够。”张齐心说。在华润给出的最早方案中,它计划将维系村中宗族情感的祠堂以异地重建的方式保留,村民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妥。但就在村民、政府和开发商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湖贝村的改造又因为另外一股力量的出现,搁置了下来。
保住湖贝
建筑师孟岩第一次看到湖贝老村时感到非常惊喜。作为北京人,他来到深圳工作之前对于它也是“从小渔村一夜间变为大都会”的刻板印象。1995年,他在深圳时正好遇上东门老街的改造,那让他认识了深圳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东门老街也叫作深圳墟,形成于元代和明代,起初是附近村庄交换物资的一片空地,至清代发展成为兴盛的集市,有东西南北四个门。到了1913年,随着广九铁路的建成通车和罗湖火车站的启用,深圳墟进一步繁荣,成为粤港两地货品的集散地,“可以说这里是近代深圳城市的起源”。孟岩拍摄到了老街在拆除前的样子,有骑楼、古井、书院等等历史建筑。“果不其然,改造后的老街这一切都荡然无存了。思月书院还在,完全是个假的复制品。”孟岩希望湖贝不要再发生东门老街的改造遗憾。
与东门相隔不远的湖贝村和深圳墟的发展过程缠绕在一起,它们共同位于深圳城市的原点。《湖贝村村史》的另一位编纂者张钜焕告诉我,深圳墟有一杆大秤,大宗农产品交易时都要经过它来保证公平,而这杆秤的执掌者一直都是湖贝村村民。湖贝村人还在深圳墟中拥有20多家商铺,“广德祥”“广昌隆”“常和隆”便是其中的名店。凡是墟市中买卖双方发生纠纷,他们即会找湖贝村中的头面人物来进行调解。除了和深圳墟的关系外,湖贝老村还和近代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相关。比如,1924年,周恩来率黄埔军校教导团东征,途经深圳时就驻扎在湖贝村,并在祠堂中开办“平民夜校”;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中,怀月张公祠是省港罢工工人的接待站,其后成为省港大罢工工人纠察队深圳支队的队部。“保留下湖贝古村,也就意味着我们能够知道今天的深圳从何处来,改变‘文化沙漠’和‘一夜之城’的观念。”孟岩这样说。
湖贝老村没有一处是挂牌的文物保护单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失去了被保护的必要。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规划系主任杨晓春的团队正在进行《深圳市历史风貌区和历史建筑评估标准》研究。该研究根据《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指标体系(试行)》再结合广东省的实际情况,制作了一套针对历史风貌区的打分标准,并把湖贝老村放在这样的标准下来判断。“这套标准的意义就在于告诉政府哪些是优秀的历史风貌区,哪怕不是文物保护单位,也有保护的依据。”可以看出湖贝老村在“风貌区整体规模”“保存体现深圳特色和典型特征的环境要素数量”“拥有传统节日、风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社会功能重要性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得分较高,总分则在随机抽取的16个历史风貌区中排名第三。评估后杨晓春建议保护的范围是1.56万平方米左右,包括南坊里中区“三纵八横”的全部,以及西区和东区的大部分。“深圳主要的历史风貌区就是古村落。1992年深圳还有1200个古村落,到了2012年统计时只有200个,10年间消失了1000个,平均每个月就少掉4个。截至2015年,尚存传统风貌区仅有150个。”现在这套标准还在调整当中,杨晓春呼吁为了保住湖贝老村,政府能够参考它的结果。
孟岩所在的都市实践建筑事务所在2012年也根据对湖贝村的独立调查做出了报告。强调湖贝村历史价值的同时,孟岩提出了城市发展中“同质化”的问题:到2017年,深圳将会有922万平方米的购物中心,相当于华润49个万象城的项目面积。距离湖贝村2公里不到就是另外一个万象城,全国有96个万象城。那么罗湖区政府到底需不需要在湖贝村的土地上,复制一个购物中心和高层住宅组成的毫无特色的地产项目呢?孟岩认为作为老城区,罗湖区拥有的文化记忆是它独特的资源。他列出了上海新天地、田子坊、成都宽窄巷子等一些历史街区改造为体验式消费区的案例:“我的态度是‘宁右勿左’,‘高大上’的活化例子我未必都赞同,但是现阶段是保住湖贝老村再说。”连同一封措辞真挚的信,“都市实践”的这套方案引起了罗湖区主管建设的副区长的重视。此时华润以及另外一家华阳设计公司已经为湖贝项目筹划了两年,孟岩的事务所参与进来,目的就是在保住古村的前提下商讨一个共赢的解决方案。
此后的过程反复而曲折。从最初华润觉得孟岩全盘保留古村的方案无法让他们利益最大化,因而不予采纳,再到孟岩带着华润的领导实地走访湖贝,他们面对老建筑时也能认可其中的价值。之后华润高层变动。最近一次发生在一个月前,罗湖区城市更新局邀请孟岩作为专家去评审湖贝村的旧村改造方案。在最新一版方案中,孟岩发现华润保留了老村西面的祠堂一片,但格局最完整的“三纵八横”和建筑最精美的东区依然要盖购物中心。于是孟岩和深圳大学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饶小军等一批建筑界和规划界的学者在7月2日和3日组织了工作坊活动,其中一个环节就是让大家动手画图。“设计的焦点是购物中心的位置以及公园的安排。我们在想,开发商如果愿意保住老村,政府有没有可能在容积率和公共绿地指标上予以让步?”
罗湖区城市更新局局长陈磊峰对工作坊掀起的舆论做出回应:根据市规划国土部门编制的《深圳市紫线规划》,湖贝村怀月张公祠被纳入了规划保护范围。除此之外,相关法律法规对湖贝旧村并没有强制性保护要求。目前有关方面正在组织编制的专项规划方案中,不仅按紫线要求落实了怀月张公祠的保护,还从较大范围对湖贝旧村南坊“三纵八横”格局予以保留。一位支持旧村保留的规划专家告诉我,这样的表态虽然比之前进步,但依然有不确定性。“一是保留的边界;二是保留的方式。迁建和重建在过去案例中都算作‘保留’的做法,只有‘原址保留’才是我们期待的。”旧改方案的最后一道程序是获得建环委的批准,孟岩等一批建筑师、学者和艺术家也在争取最后的时间来为老村做最大限度、原汁原味的留存。他们行动的一个方式是争取更多的公众参与和支持——近来不断有行为艺术家在村中的巷子里表演,也有志愿者带着学生来参观。租住者对于外来者好奇的眼光,已经见怪不怪了。
谁的村庄
湖贝村是特殊而幸运的。同样属于城中村,其他村子面临改造时可能根本没能经过讨论,就被拆掉了。“岗厦村和蔡屋围就是如此。因为它们就在深南大道边上,这就相当于北京长安街边上有个村子,根本没得商量。”孟岩说。湖贝村则正好有湖贝路作为遮挡。另外一个原因是,湖贝村的老村具有历史价值,建筑成规模地完整保护下来,使得用“保护城市历史”来捍卫老村成为可能。而对于其他的城中村,基本都是在原址上将老房子推倒重建,没有历史变迁的痕迹,“想谈保留,却很难唤起人们的共识”。对于湖贝村的研究,孟岩等专家学者是将它放在城中村对于城市意义的框架中来看待的。
作为移民建设出来的城市,城中村对于深圳的贡献不言而喻。“不是来了就是深圳人,而是来了先当村民,出来才是深圳人。”在深圳从事城中村研究的美国文化人类学者马力安这样说。《落脚城市》(Arrival City)的作者道格·桑德斯用“落脚城市”一词来形容乡村移民进入城市时所暂时居住的地带——他们在这里完成适应和融合,“成功的落脚城市都是创造新兴中产阶级、消除农村贫穷现象以及终结社会不平等的关键因素”。在不同的国家地区,落脚城市有着不同的名字,比如法维拉、巴斯蒂、贫陋市镇或者都会贫民窟,那么在深圳,它就是城中村。孟岩回忆,大约在2005年左右,深圳开展了名为“静畅宁”的城市美化行动,城中村被看作藏污纳垢的典型,从中清走100多万人。同年开始的第一届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关注到城中村的话题,之后每届都会谈论城中村。“当年大家对城中村的印象是完全负面的,今天却能思考到它承载的社会功能。讨论湖贝村的历史价值,只是个开始。”
7月3日,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教授在参观湖贝旧村时,惊叹它是“活着的古村”,与他在全国许多地方看到的徒有华美建筑而已经人去房空的村子截然不同。为古村带来生活气息的不是原住居民,而是潮汕移民。潮汕人多在深圳经商。20世纪90年代初,湖贝村民集资建设了一座湖贝东门市场,它一度是全国十大肉菜市场之一,瞬间吸引了来自潮汕的摊贩。市场里来自潮汕不同区域的人把持了多种农贸产品的交易,海鲜类一定是陆丰人在做,其他卖蔬菜水果的有可能来自揭阳。
租户在城中村的改造中始终是被忽略的群体,他们并不拥有产权,究竟是拆还是留似乎也不用征求他们的意见。1992年出生在南坊的钟美玲在湖贝村生活了14年。她告诉我,父母都是在东门市场做海鲜批发和配送生意的,直到后来换到另外一处罗芳海鲜市场,她家才彻底搬离湖贝村。“从记事的时候起,村里就有要拆迁的传闻。父母那时常感叹,这下找房子换工作可麻烦了。但是一直都没有动静,也就有了一种‘狼来了’的适应,每天照常生活。”即使离开了湖贝村,她家离湖贝村也不过四站之隔。“妈妈经常会来湖贝村买家乡的食品和祭祀用品。那些摊主和往来于潮汕与深圳之间的客车司机都很熟,可以让他们随时‘夹带私货’。小时候妈妈做饭,有时候就会特地提醒我,这是老家的东西啊,味道更正宗的!”钟美玲的妈妈还会每星期回到村子里找一位独居的阿婆。那位阿婆供奉不同的神灵,妈妈会给她香火钱让她帮忙拜神和传达心愿。在钟美玲的记忆里,湖贝村完全就像是潮汕老家村庄的翻版,一个有着浓郁宗教信仰和靠乡情网络维持运转的社会。
与钟美玲的情况相似,另外一位郑千安也是在湖贝村出生的“深二代”。他的父母如今仍住在湖贝村的楼房里,他则在和湖贝村隔着两条马路的地方租了自己的公寓。“很奇怪的感觉,这里不是故乡但是会有故乡般的亲切感,所以一定要挨着它住才会心安。”从事文化传播工作的他并不认为老村应该保留下来继续留给潮汕租户,“将建筑保留下来经过修复后另作他用,或许是对村民和租户都公平的一种做法。”
我在村子里还遇到了周晓燕——一位来自陆丰的第一代打工者。她的丈夫和哥哥在东门市场卖海鲜,她一度在东门步行街的小店里销售服装,现在在家带两个孩子。深圳的教育资源也是她想留下来的原因。她说,如果村子拆迁,大概会先回老家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深圳找工作。“工作倒是不难找,但就看能不能是自己称心如意的了。”她给我看手机里的照片,那是中秋节的场景,老村里每家每户都在门前摆出了五颜六色的祭品:纸扎的花篮、水果、香烛、月饼……完全是潮汕乡间的气氛,带给漂泊在外的人以慰藉。
深圳设计促进中心高级研究员傅娜,和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生布雷热(J.Cressica Brazier)曾经就岗厦村的搬迁对于租户的影响进行过调查。他们发现,搬迁后大部分租户的居住条件都得到了改善,但是居住在靠近工作地点的机会更少了,搬迁也削弱了他们原来建立的社会关系网。一个有趣的结果是,这些搬走的人们会间接地给城市交通造成压力——他们会买车,不仅是居住的地方上班通勤需要用车,而且也是提升社会认可度的选择。傅娜的调查人群以年轻的专业人员为主,而对于那些租住在城中村里从事服务行业的外来务工者,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他们搬去了更远的地方居住,人们享受着他们提供的服务,却看不见他们每天辛劳奔波的状态。打工者为这座城市奉献着青春,依然无法享受到城市给予的福利。
当人们讨论湖贝旧村的去留时,也是在讨论它作为城中村在未来的更多种选择。在孟岩看来,城中村业态多元、充满活力、日夜不息,以其独特的社会生态丰富了城市的多样性。无论政府还是村中的股份公司,加大投入对村里的硬件进行改善、业态进行升级都是十分可行的第三条道路。在深圳最大一片城中村“白石洲”,我看到它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城中村”,而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成为一片“城中城”,不少白领都居住在那里。甚至它还有美国人开的自酿啤酒坊,意大利人开的电子音乐酒吧,成为一片国际化的区域。“只要保留下来,活化就有多种可能。前提就是保留。”(实习记者唐瑶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