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晓都 孟 岩 王 辉
出版 景观设计学 2008(2):28-29
作为一个立足于当代文化的建筑设计事务所,介入景观设计领域是URBANUS都市实践主要的实践策略之一,而“城市填空”是URBANUS都市实践景观设计的基本策略。
较之于建筑活动,人类的造景活动更有文化色彩。造景活动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它是超越了基本生存之外的享受,是人类内在精神在天地之间的释放。如果说文学是对不完整的生命界的补充和补偿的话,造景则是对不完美的居住界的补充和补偿。姑且不论古代帝王用瑶台仙境般的景苑来烂漫化短暂的人生,文人墨客用隐于俗世的私家天地来逃遁尘世的险恶;当今的开发商们也长于用景观来包装商品,政治家们更乐于用景观来粉饰太平。在这个层面上,景观设计必然会与意识形态瓜葛,即使它在回避政治,政治也会来敲门。
之所以只是抒情发感的景观会与意识形态有不解之缘,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是能驾驭景观控制权的人必然是集体资源的拥有者和统治者,他们的理念已超越了个体的好恶,而代表了主体的社会意识形态。一是景观又要面对公益的审判,少数人的意志要博得公众的喝彩,因而景观设计中又包含着意识形态游戏中的无限玄机。如果历史从来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力量的演绎,上述的两个层面应当会使让人闻到景观设计中的火药味。然则现实中的景观领域则波澜不惊。昔日帝王苑囿成了今天的人民公园,似乎毫无意识形态上的冲突,甚至还会庆幸当年海军军费没有打水漂。在当代商品交易中,卖家为迎合买家而生的景观设计更是令人乐也融融。这也揭示了景观设计的某种本质:由于它是让人在不足中知足,在陶醉中忘却,所以它具有极强的蒙蔽性。
这种蒙蔽性不只是针对被动地来享受景观的大众,还作用于许多没有立场的景观设计的主角设计师们,他们更多地是用技术层面的专业操作来发挥景观设计的粉饰作用。这种作用不是不必要,也不是没有业绩,更不是大众不喜欢。但在当今中国城市化条件下,设计师脱离了意识形态的思考,既是对时代机遇的错失,也是对历史机遇的不负责。URBANUS都市实践在近十年的景观设计实践中,始终坚持的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批判性,并不是唐吉坷德式的臆想,而是有其迫切的时代性。
理解设计师的角色,必须要去看他们的时代背景。当前这个背景有三个现象:一是疯狂的城市化使设计量与设计能力的比值超常;一是新技术和文化的创生与时段的比值超常;一是评判社会生产效益的价值尺度又超常地单一。这种背景使设计师们很困惑。一方面他们是骄傲的巨人,即使是个小人物,也控制着史无前例的资源,可以调遣技术和说辞的十八般兵器;一方面他们又处于剃刀的边缘,既无以招架超负荷的任务与信息,又无以抵挡一切以经济利益为准绳的价值指导。因而,在时代的大机遇面前,反而很窘迫,放弃了主动的思考,而成为被动的技术型设计工具。民主社会更是一个利于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温床。景观设计师搅尽脑汁地去包装商品、粉饰太平过程中,回避意识形态的冲突过分地去迎合大众口味,而没有创造性地去引导和诱发大众的新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历史性的遗憾。
在景观设计领域,坚持批判性实践的URBANUS都市实践,有三个意识形态的命题思考。
- 公益性。景观设计是面向公众的设计,体现了公共的利益。但公益性本生具有极大的歧异。一些商人或政客的御用设计师也往往乐于在公益性上大做文章,把公益性狭隘地定义为大众的满意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大众的不质疑度。因此,所谓公益,成了好好先生的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 不敢去触及敏感课题,回避有争议的挑战,把政治游戏的原则凌驾于设计原则之上。制作公共文化的意义在于教化,设计师如果没有高于使用者和决策者的专业想象力和操作力,就好无被雇用的必要。因此,一味地迎合甲方、迎合市场、迎合所谓的大众口味,事实上是愧对甲方的委托。设计师最大的公益心是用设计来传达时代的先进理念,为大众启明。
- 当下性。用景观来弥补建筑环境的不足恰恰是景观设计的最大来源,这也造就了意景观空间和与其所处的建筑环境的错位。景观设计是跨时空的艺术,但人们往往不去畅想用当代时空和未来时空历来改变现实,而更多地乐于把历史上的、其他地区的造景方式移植到当下。诚然,简单地移植成熟的文化形态不会有任何危险,也容易形成大众化的审美愉悦。但当今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人文条件从理论上是可以造就特殊的文化,形成新的知识。我们的设计师拥有令人艳羡的设计条件,却无志于创造新文化,既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也是对社会的不负责。十年前,库哈斯重拾“大跃进”来定义中国目前所处的时代。这个定义的不准确之处是虽然目前的跃进比起近半个世纪前的“大跃进”更跃进,但它几乎完全丧失了公众狂热的理想主义色彩。当今在创造人类经济史的奇迹时,整个中国市民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小康思想;在讲究人性化的同时,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停留在小我私利的计较之上。诚然,这样的意识更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和实用性,但面对这个时代的机遇,如果再有一些乌托邦式的热情的话,中国贡献给世界乃至整个文明史的东西也许能更多一些。这种乌托邦式的热情并不乌托邦,它是建立在中国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热望之上,建立在中国拥有当代先进生产力的产能之上,建立在中国不断涌现出的富具创意才华的设计人才之上,更建立于中国城市决策者的雄心之上。这种客观条件的东风是中国城市的诸多现实矛盾,它既不能靠巴洛克式的城市美化来粉饰,又给当代景观设计拓展了无限的外延和丰富的内涵。当代问题要用当代文化来解决,只有以创造当代文化为己任,才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 参与性。在城市公共空间领域,中国有专门的政府职能部门负责其规划设计、实施和维护;在个体开发领域,有专门的规划条件来界定开放空间指数(建筑密度和绿化率),这使中国城市极具有有完善的公共空间系统的潜能。但是,这种巨大的优越性的效能很低,终其原因在于中国城市公共开放空间往往被定义为绿地,成为绿化工作的主战场。在行政职能条块分割的现实环境中,过分的围挡式绿化使公共空间的社会职能很难得以实现。这种社会职能首先表现在公共空间是行为上公众共享的场所,而不只是视觉上的观赏对象;其次城市活力来源于城市活动,因而公共空间是城市的活动场所,而不是美化的对象。如何让市民能真正参与到城市公共空间领域,是景观设计中最有价值的创意。
基于上述的意识形态思考,URBANUS都市实践的景观设计立场是清晰的,即如何在当代城市景象中植入有生命力的元素,使城市生活更有人性的魅力,亦即我们所提倡的都市性。植入,顾名思义,是在某种基础上的介入。这也表明,我们从来没有低估和否认其他人在塑造新城市的努力,没有他们的努力,可能也没有我们实践的基础。当我们也看到,在快节奏、高产量的压力下,许多设计缺乏批判性,因此即使没有错误,也还是有缺憾。这样,时代就需要另一批设计师来弥补这种缺憾。这也使我们所谓的“都市填空”的渊源。

“都市填空”目标之一是针对当代物体城市(object city),如何用景观设计的手段来联系支离破碎的城市片断。URBANUS都市实践的第一个委托项目即使深圳地王大厦周边的城市景观设计。通过我们的设计,被闲置的城市废地重新联结起来,成为市民们体面地城市客厅。有趣的是,URBANUS都市实践参与过的所有景观设计中,鲜有封闭社区的庭院设计,而几乎都是城市中被忽略的公共空间的设计。这些设计都围绕着如何借助环境整治来实现连续的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系统:一方面满足人们对高品质的公共空间的需求;另一方面用这一计划去填充那些在高速建造城市过程中剩余下的边缘空地,进而织补支离破碎的城市外部空间。我们尝试用都市造园的手段逐步去梳理、连接、充实和转化高速城市化所形成的“物体城市”。每一个“景观设计”项目都可以当作一次从城市局部对更大范围的周边地区实施作用的机会,来修正和重新建立建筑物与城市公共空间的联系。
“都市填空”目标之二是针对于当代移民城市,如何用景观设计的手段重新建立起人和人的关系,以及人和土地的关系。移民是当代城市的特征。即使人没有动,城市也在变。城市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陌生的。在天津塘沽碱渣山住宅项目景观设计中,用无数的运动场地来代替绿地,目的是用体育来形成邻里交往的平台。在深圳翠竹公园入口设计中,通过把自然台地变成可种植的梯田,让周边居民来认领,既节约了市政开支,又产生了居住着和居住地的链接。这些努力证明了帮助居住者和城市建立起心灵的纽带,是景观设计者的责任。
“都市填空”目标之三是针对当代城市的乏味,如何用景观设计的手段来搭建都市舞台。城市的乏味不是视觉的单调或不雅造成的,而是生活的枯燥带来的。如火如荼的城市化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是对城市量的扩容,反而更造就了内容上的空虚。假如把城市化理解为框架式的搭建,去用有意义的项目来填空这些空框架,其意义远大于用装饰的方式来美化这些空框架。深圳笋岗广场很好地证明了在最无聊的物流空场中,人们多么渴望人文化的景园。天津泰达城计划中,通过把绿地定义为胡同式的走廊,使邻里的各种交往活动都能发生,尝试了用景观设计的方式来弥补排排坐、板凳式的规划布局遗憾。
“都市填空”目标之四是针对当代城市政治空间,如何用景观设计的手段来使之平民化。大规模的城市景观建设,往往源于城市的决策者,因此,它们必然有着浓烈的政治色彩。而景观构图的许多手段,也恰恰对塑造政治空间得心应手。对于当代亲民的政治导向而言,如何使政治空间平民化,既需要理念,也需要技巧,还需要勇气。深圳宝安新城广场便是面临这一棘手的课题。在市府面前,如何平衡城市决策者和城市打工者不同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是对设计师设计能力和推销能力的全面考量。同样,对北京奥运广场城市标志物的提案,也体现了我们始终如一的关怀城市平民的理念。
“都市填空”目标之五是针对当代城市的守旧,如何用景观设计的手段来植入新的文化。之如开篇所言,由于景观设计的容易用美观来博得喝彩,使之有强烈的蒙蔽性。许多景观设计都是在宣扬政治上正确的保守文化。新文化的宣扬是景观设计中要填补的重要空白。深圳罗湖公共艺术广场(现罗湖区文化馆)原先是一个充满世俗气息、被遗忘在都市角落的停车场。在最没文化的地方,我们设计了一个生动的、另类的城市生活舞台,创造了一个公众触摸艺术的界面。这种文化氛围的引入不是城市演进中自然而然发展的产物,而是一项精心策划的文化注射。在CCTV媒体公园提案中的电视广场,提供了一面起居室式的墙面,无数屏电视象从墙缝里绽出的鲜花,吸引路边的行人。电视曾是把人离散到各自居室里的力量,但这样的街头电视墙又把人重新凝结到公共空间之中。这些设计实践展示了当下有无数的话题,可以在实际中展现,而无需在没落的老生常谈中去接受灵感。
“都市填空”目标之六是针对当代城市所要面临的未来,如何用景观设计的手段来采取新的城市生态策略。景观设计的最大误区是把绿化和生态划等号。绿化只是生态的必要条件,城市生态的目的不是养树,而是养人。生态的终端是人,让个体的生命如何得到了自然界的滋养。许多城市绿化并没有使人获得在绿化环境中的享受和解脱,个体不能主动地介入城市生态圈,生态的目的也无以完成。面对当前的城市在疯狂地吞噬乡村,在上海嘉定复华科技园的设计中,利用已有的农业耕地,把农业作为未来城市中心区景观建设的主体,从而使城市人能够在日常的办公环境中就回归到乡村。面对城市中有意整理出的绿地,唐山博物馆公园有意保留一部分工业遗址,将之改造为博物馆群,使人们乐于来享受公园。在深圳未来城市光明城中心公园的提案中,利用分散的启动区使城市活动切入三倍于纽约中央公园的中心绿地,并利用这些活动来支持公园的深度开发。这种可持续的开发策略,也是对城市生态的思考。
面对设计课题,设计师能回避意识形态的提问吗? 显然,任何人都不能回避立场问题,没有立场也是一种立场。面对当今的时代机遇,意识形态的选择非但不能回避,还更加关键。假如URBANUS都市实践有什么特别的话,其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思考过意识形态问题,在于它既为意识形态问题付出过代价,也为意识形态问题享受着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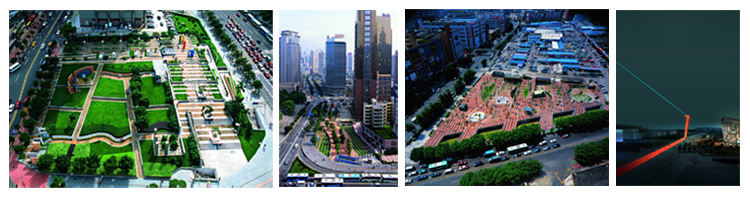
本文发表于《景观设计学》2008/02 p28-29
